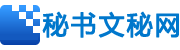【www.rconcon.com--热门资讯】
想知道1937年袁牧之导演的电影是什么电影吗?想知道的就快来吧!以下是本站分享的1937年袁牧之导演的电影是什么,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1937年袁牧之导演的电影是什么

1937年,由袁牧之执导,赵丹、周璇等人主演,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是( c )。
A、《十字街头》:
B、《乌鸦与麻雀》
C、《马路天使》
D、《烈火中永生》
革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新中国首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
袁牧之,原名袁家莱,浙江宁波人,1909年4月12日出生。我国优秀的戏剧、电影演员、编导,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和最早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电影局第一任局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病故。
戏剧生涯
袁牧之的父亲袁子壮是一位与洋人做生意的买办,他曾经娶过几房妻室,但是子女多数夭折,在袁牧之出生之前,家中只有一位年龄大他许多的姐姐。袁牧之的母亲过门后生了一子一女,袁牧之5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不久母亲携其妹改嫁,袁牧之作为这个家庭的独子,由前房的夫人养育成人。这位由尼姑还俗的妇女心地善良,视年幼的袁牧之如同己出,不仅非常疼爱,而且给他提供了最好的教育条件。对于这位养育自己成人的母亲,袁牧之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情。1929年3月养母去世时,袁牧之特地赶回宁波奔丧,后来他在文章中特别谈到了养母去世时的难过和悲伤。
袁牧之幼年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时,即已表现出对于文艺的爱好。10岁时,养母将他送到上海读书,由在上海海关工作的姐夫和姐姐照顾生活,每次放假回家,袁牧之都和童年玩伴一起,自编自导自演一些小戏给养母和乡亲们看,他把家里的衣服拿出来当“演出服”,给小伙伴们穿上,演出时,他经常一人串演很多角色,这时的他已经开始显露出表演才能。
上中学期间,袁牧之先后担任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和主席,同时开始在学校中参加业余演剧活动;在校长的帮助下,他逐渐培养起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在校期间,他曾代表学校参加了浙江省的学生演讲比赛,获得第三名,返校时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15岁时,袁牧之加入了应云卫、谷剑臣、欧阳予倩、洪深等主持的戏剧团体戏剧协社,成为剧社中惟一的小演员。戏剧协社的正规排练和演出实践,不仅为袁牧之一生的表演艺术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中国的话剧艺术始终贯穿着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对袁牧之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7年,刚满19岁的袁牧之进入东吴大学学习法律。读书期间他加入了朱穰丞先生主持的辛酉剧社,先后扮演了俄国安德列也夫编剧的《狗的跳舞》中的翟汉礼、俄国契柯夫编剧的《文舅舅》中的文舅舅等主要角色。由于他在演出时总是力求把握住人物的个性特质,善于在舞台上脱去自己的生活形态,而以真挚的演技,准确而有层次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成功地创造了许多艺术形象。他的演技受到戏剧界的重视和观众的欢迎。除演剧活动外,他还在课余时间坚持写作,在1928年、1929年分别出版了独幕剧集《爱神的箭》、《两个角色底戏》。
袁牧之的剧本创作并不是象牙塔中脱离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它们比较集中地再现了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感情。《叛徒》中男女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揭露了战争的无情和世态的虚伪;《寒暑表》揭露了小知识分子生活的空虚和无聊;而他1932年创作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其构思之精巧,人物之生动,女角色嬉笑怒骂,将警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机智,都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感染力。袁牧之认为在舞台上,两个角色演出的戏最为适合,所以他的第二本剧集全部是为两个角色所写,书名也就叫做《两个角色底戏》,而《一个女人和一条狗》更是淋漓尽致地为两个演员提供了创造角色的基础。这些剧作是袁牧之戏剧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巧妙的取材和丰富的舞台性,曾使朱穰丞先生感到惊异,他预言袁牧之将来必定会有杰作出世。袁牧之早期的表演和剧本创作活动尽管只是在艺术的道路上刚刚起步,但是他一开始就走上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正确道路,并在此后的艺术实践中继续了这一方向。
就在年轻的袁牧之积极投身演剧活动和剧本创作的同时,中国社会和中国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革:1927年的“四一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革命而宣告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横征暴敛,欺压百姓,一方面从军事和文化两方面对革命势力进行“围剿”;而日本帝国主义也趁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文化侵略。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成立了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从此开始过问和领导文化工作。1930年3月1日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戏剧、美术、音乐、电影等各个艺术门类都先后成立了不同形式的左翼文艺组织,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左翼戏剧运动的兴起,对于年轻的袁牧之的艺术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被吸引加入了左翼戏剧运动的行列。但是他的志愿与姐姐和姐夫的期望相悖,他们遂以停止经济支援相要挟,袁牧之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他们脱离了关系,并从此走上了职业演剧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先后扮演了洪深编剧的《五奎桥》中的赵乡绅、田汉编剧的《回春之曲》中的老华侨、苏联特列泰柯夫编剧的《怒吼吧!中国!》中的老船夫等角色。
在舞台实践当中,袁牧之认为一个艺术家是要有灵魂的。他认为:“一个演剧家是不仅依仗他的技巧,他还要体味剧作家的理想,要在上演的时候,把剧作者在剧本中造成的角色的灵魂放进自己的躯壳里去,使自己完全变成了角色①。”
他非常重视演员表演的技巧,他认为演员应当能够在不同戏中创造不同的角色,在台上把化装、发音、动作都脱离了自己而变成剧中的角色。为此,他对于自己在表演时的化装、发音、动作等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他在舞台上创造了各种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获得了“千面人”的美誉。
他还非常注意生活的积累,他把这称之为“加作料”。他说:“所谓加,便是剧本上没有,而要演员自己加上的。所谓作料,是用来帮助演员表演的,使更像角色的杂碎的小动作,作料要预先有大量的进货,然后派到角色的时候才可选择而应用,进货的来路是随时随地的观察。”②为了在《文舅舅》中扮演文舅舅,他曾经在排练这出戏的三个月中间,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到俄国西菜馆去吃饭,观察在那里吃饭的各色各样的俄国人,从中不仅解决了服装和化装问题,更从中观察他们的神态、表情和目光,以用于文舅舅的身上。
袁牧之在他的话剧演出生涯的大量实践中,显示出他具有的天赋和才能,这使他进入优秀话剧演员的行列,并且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
在进行表演艺术实践的同时,袁牧之非常注意不断总结自己的表演艺术经验,对于艺术理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钻研,先后写作出版了《戏剧化装术》和《演剧漫谈》等著作。《戏剧化装术》是我国最早介绍话剧化装术的专著之一。这本书在系统性与科学方面,不仅超过了当时的同类著作,而且多年来在同类图书中亦为翘楚。《演剧漫谈》是袁牧之长期登台演剧的经验之谈,显示了袁牧之对于艺术和人生的严肃科学态度和丰富的知识底蕴。这两本著作虽是入门性质的读物,但袁牧之把富有学术价值的人生体验和艺术体验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述出来,不仅受到专家同行的重视,而且引导许多电影戏剧的爱好者走上专业道路,曾经有人说“我就是捧着这两本书走进戏剧艺术大门的”。至今这两本书仍然受到欢迎和重视。
袁牧之那时几乎同所有的职业演员一样,没有固定收入,除去剧团有戏演时可以有一点微薄的收入外,他还有一点稿酬。有收入时他可以租间房,也可以上饭店吃饭;没收入时他就随便在哪个朋友家住住,有时也在朋友家“混饭”吃,在混不上饭的时候,饿肚子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种近似流浪的生活并没有阻止袁牧之投身戏剧创作的热情,相反,这成为他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生活积累。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对上海的这段生活仍然具有深刻和美好的记忆。
电影创作
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之初制定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中,为左翼剧联在白色区域开展戏剧运动制定了六条纲领,而在这六条纲领当中,有三条是关于电影工作的。正因此,左翼电影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
1931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上海。日寇的轰炸,使许多电影制片厂的厂房和设备受到严重破坏,电影制片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而在此前,上海规模较大的两家电影制片厂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所出品的影片,内容多为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电影观众的主要成分是城市小市民阶层。联华公司成立后虽然实行了新的制片路线,开始建立了知识分子观众群,但是所能起到的作用对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电影的面貌来说还只是初步的尝试。“一·二八”战火,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空前提高,他们不愿意再看那些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的电影,电影市场严重萎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电影制片者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的良心被唤醒,一方面处于市场的严酷形势,促使他们必须改变制片方向以适应时代和市场。这时,首先采取行动的是明星公司的三位老板——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他们接受了公司导演洪深等人的建议,把改变制片方向的目光投向年轻的左翼作家。
左翼文艺家对这个机会采取了十分积极而又谨慎的态度,因为生产资料毕竟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进入电影界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心中无邨数。在钱杏向“文委”报告了明星公司邀请左翼作家加盟一事后,“文委”召开了多次会议,与会者持有不同的意见,进行了多次激烈讨论和争论。最后得到中央负责上海地区文化工作的瞿秋白和“文委”的批准,左翼作家很快向电影厂交出了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还对其他导演的剧本提出意见,于是在1932年底和1933年初,田汉、沈端先(夏衍)、阳翰笙、沈西苓等一批左翼作家的第一批左翼电影问世。同时,团结电影界各方面人士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和以沈端先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也在这时先后成立。
左翼电影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文艺运动。共产党人进入电影界后,除了因抓剧本而介入电影创作之外,还抓了电影批评、外国电影理论介绍等工作,在组织方面,有计划地把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音乐小组、左翼美术家联盟等组织中的成员输送到电影界。在左翼戏剧运动中具有社会影响的袁牧之,这时被党组织由左翼剧联输送到电影界,被安排到由党的电影小组领导影片创作的电通公司工作。
电通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袁牧之为这部影片写作了剧本,并在影片中扮演了男主人公陶建平。袁牧之在这部初上银幕的处女作中,用自己深厚的表演功力,把陶建平表现得准确生动。在编剧和主演这部影片时,袁牧之调动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对电影表演的分寸感非常注意,这一点在当时评论中曾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部影片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许多青年就是唱着这部影片的主题歌《毕业歌》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部影片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慌,有人写文章攻击这部影片是苏联影片《生路》的翻版。其实,这两部影片仅就内容来讲,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可见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
袁牧之在电通公司主演的第二部影片是《风云儿女》。他在影片当中扮演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青年诗人辛白华。在这部影片中,袁牧之紧紧把握住辛白华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善良正直和追求进步的人物基调,把他走上民族解放战场的思想基础和从诗人到战士的发展转变过程表现得生动感人。袁牧之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较之《桃李劫》有明显的提高,表演中的设计和人为的痕迹渐少,而愈显得浑然质朴。特别值得一讲的是,在这部影片拍摄过程中,剧作者之一田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作的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他的女儿带出后,由聂耳谱曲,成为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在影片当中演唱这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曲的,正是袁牧之和他年轻的同志们。
袁牧之是一位艺术上的有心人,经过两部影片的表演实践,他又迈出了新的一步,编剧并导演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把自己扮演的放映西洋镜的老人当作影片故事的讲述者,而影片的全部故事,就是他所放映的西洋镜中的故事,这种结构方式在当时也是最早的尝试。袁牧之在拍摄这部影片一年多以前产生了“为什么中国不会产生出几部音乐喜剧片来呢”的想法,在拍摄这部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部音乐喜剧片时,他明确地认为:“音乐,我想不该是几支主题歌或是几支听厌了的西洋老调所独占的,所以,我试想着能在这里贡献些其他部门的新鲜音乐。喜剧,我想不该是跌跌打打的噱头或是哭哭闹闹的低级趣味所范围的,所以,我试想着能在这里贡献些能在笑里显现出丑恶的笑料③。”于是,他请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为孙师毅的歌词谱曲,写作了由放映西洋镜的老人演唱的《西洋镜歌》,这首歌是由袁牧之自己演唱的。当时,刚刚以一曲《牧童短笛》获得国际音乐奖的青年作曲家贺绿汀也应邀为这部影片中的卡通片断创作了一段诙谐生动的卡通音乐。这部影片中人物所有的动作都配有富于戏剧性的音乐,担任音乐编辑的是吕骥。这部影片的成功,显示出中国有声电影的制作开始走向成熟。袁牧之在导演影片时,非常重视音乐在影片中的能动作用,在中国的电影导演中,袁牧之是最善于运用电影音乐的导演之一。
电通公司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它的正式出品也仅仅只有四部影片,但这四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其中袁牧之担任主要创作人员的就有三部之多。这不仅显示了袁牧之在艺术上的成熟,更显示出他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参与左翼电影创作后,在政治上也有了明确的抉择。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电通公司日益扩大化的影响感到恐惧,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拔掉了这个令他们日夜不宁的眼中钉,但是这并不能扼杀左翼电影的影响,更不能阻止广大电影观众对于左翼电影的热爱和欢迎。不久,电通公司的领导人经过与明星公司领导人的磋商,组成了以电通公司的创作人员为主的明星公司第二厂,袁牧之也随之到了明星公司二厂。
此刻已经到了1936年。从1932年开始的左翼电影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也作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艺术革命运动,已经逐渐成熟。一批思想深刻、艺术感人的影片接连问世,左翼电影也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导演和明星,袁牧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明星二厂,曾经参加过大革命的左翼作家阳翰笙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出了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在这部影片当中,袁牧之一人扮演了李涛和柳元杰两个角色。李涛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党领导人,面对敌人他坚定勇敢,有勇有谋,对待人民群众他细心呵护,对年轻的革命个倾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黑暗的社会势力他富于正义感,对自己的爱人他一往情深,但是斗争经验未免不足。这两个人身上有共同的一面,更有不同的方面。袁牧之在表演当中强调了两人的不同,对于李涛,他强调他的成熟和坚定,造型上则比较老成,后来又加上面部烧伤;而对柳元杰则强调他的年轻甚至略显稚嫩,在造型上还适当地加上了俊美的成分,这样两个人物就有了很大的区别。袁牧之认为自己在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花费了不少苦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编剧者的创造尚有主观的自由;而演员的创造则必须受到许多客观理由和客观环境的限制。实际上,也因为演员的创造需要是客观的创造,所费的苦心有时也会超过编剧者,譬如我这次《生死同心》的角色,就费过两星期以上的构思,和六七次以上的试验④。”
《生死同心》演出后不久,袁牧之开始了影片《马路天使》的创作。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的一朵清新美丽的奇葩。它以极其流畅的电影语言表现了生活在上海最底层的歌女、吹鼓手、妓女、报贩、理发匠、小贩等人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在污浊的环境里所保持的纯洁心灵。影片所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熟练的导演手法,使它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也使袁牧之成为中国电影导演大师。袁牧之是演员出身,他在这部影片当中对于演员的选择和使用令人拍案叫绝:赵丹、魏鹤龄等这些已有成就的演员,在这部影片中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异彩;而只演过几个小角色的歌唱演员周璇被袁牧之慧眼相中,选来扮演女主人公——歌女小红,她与小红类似的生活经历、她的具有独特韵味的演唱,以及她稚嫩纯真的相貌,都使她成为扮演小红的最佳人选。经过袁牧之的导演,她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光彩的女性形象之一。曾经在曹禺先生的名剧《雷雨》中出色地扮演了蘩漪一角的赵慧深,在影片当中扮演了只有一句台词的小云,她的富有表现力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苦难中的女性角色,从而使这个一生只演过一部电影的女演员在中国电影史上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在这部影片里,袁牧之还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许多如隐喻手法等经典的段落。在这部影片里,袁牧之与自己的老搭档贺绿汀合作,让他用江南民歌的曲调为田汉写作的两首歌词谱曲,写作了《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由周璇演唱。这两首歌成为影片剧作的一部分,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感情的交流、人物关系的变化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由于这两首歌的写作和演唱均属一流,影响经久不衰。这部影片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复映,80年代后更是多次到国外放映,获得了国外电影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1937年,抗战爆发后,袁牧之与上海戏剧电影界的艺术家们一起,积极投入了抗日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他还是导演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随后,他与许多进步的电影话剧演员一起,来到了当时抗战的领导中心——武汉。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担任了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属的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担任主任秘书。三厅所属的负责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第二科,主管电影制作和放映。
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时,在他的南昌行营“政训处”下就有了一个电影制作单位——“汉口摄影场”,专门拍摄为蒋介石“剿共”服务的影片。当“政训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改由政治部领导时,“汉口摄影场”同时改由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并改组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厂长郑用之,阳翰笙兼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参加“中制”,袁牧之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中制”的工作。在“中制”,袁牧之主演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这部影片是根据不久前发生在上海的抗战英雄的真实事迹拍摄的: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顽强抵抗日军;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也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尊敬。在这部影片中,袁牧之把谢晋元强烈的爱国热情、大敌当前时的坚定,以及军人的责任感,还有他个性中的冷峻、富于决断等,都表现得极具鲜明的个性。袁牧之第一次扮演军人形象,他通过对于一位中层军官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丰富了自己所创作的人物群像。
袁牧之在上海和武汉的电影创作生涯中,为中国电影留下了陶建平等一批闪烁着时代理想光辉和鲜明艺术个性的银幕形象和《都市风光》、《马路天使》等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如果说中国左翼电影曾经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那《马路天使》就是立于这个高峰之巅的作品之一。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也奠定了袁牧之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和导演艺术家的地位。
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组织者
在武汉,袁牧之一面从事影片《八百壮士》的拍摄,一面一如既往地参加电影界的各项社会活动,如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为《抗战电影》杂志组织的关于抗战电影的前途的讨论写文章。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思考日益清晰,他找到了当时在主持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向周恩来表示自己要到延安去,用电影为工具为革命作贡献的愿望,经过深谈,周恩来决定派袁牧之到香港去购买器材。在香港,袁牧之得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等同志的大力支持,购得了包括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等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及数万米胶片。
袁牧之回到武汉的时候,国际著名的荷兰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正在中国拍摄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但是,他的拍摄工作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方限制和掣肘,令他不满意。周恩来在这时写信给三厅厅长郭沫若,指出“三厅应支持伊文思拍片⑤”,在信中,他还详细地交待了如何为此事与国民党打交道,以及人员的配置安排等。从此开始,伊文思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周恩来的安排,他拍摄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会议和活动。在他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与袁牧之见了面,两人长谈数小时,非常投机。当伊文思得知袁牧之即将到延安去拍摄电影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的摄影机和剩余的胶片送给袁牧之,让他带到延安去。
1938年秋天,袁牧之和他长期合作的创作伙伴吴印咸一起携带着所有的器材和胶片,辗转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很快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团长,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曾经参加过宁都起义和长征的老红军李肃负责政治和行政工作。
到延安,是袁牧之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阶段。这个全国革命的摇篮所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抗日军民的革命热情,深深感染着袁牧之,以至于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困难都不能影响袁牧之的创作热情。在延安电影团成立后,袁牧之立即着手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他写作了详细的创作提纲。之后,他们在延安拍摄了一段时间,1939年1月,摄影队从延安出发到华北敌后去拍摄,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作了宝贵的指示,还请他们吃了饭。
《延安与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和八路军战斗生活的实录,是一首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光辉诗篇。摄影队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兵分两路,袁牧之在晋东南,吴印咸在晋西北及平西,经过将近一年的深入抗日前线,在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工作,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素材。贺龙同志任师长的129师政委关向应同志与袁牧之一起返回延安,在途中,他和袁牧之谈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袁牧之表示“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条件,还需要好好学习”。关向应说:“入党以后可继续学习嘛!”他还表示愿意做袁牧之的入党介绍人,袁牧之当时非常感动。回到延安后,关向应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介绍袁牧之入党的信。不久,袁牧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进步艺术家成为一个党员艺术家。不久,关向应同志因病逝世。袁牧之对关向应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每次提到他都不禁热泪盈眶。
1940年3月,《延安与八路军》后期制作的大量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中共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和担任《延安与八路军》作曲的“鲁艺”教授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这部影片的后期制作,同时对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进行学习和考察。
除《延安和八路军》外,延安电影团还拍摄了《白求恩大夫》。在袁牧之离开后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即《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影片。这些影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道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以及他们的风采。这些影片成为中国人民永久的珍贵历史资料。
到苏联之后,袁牧之把影片的全部素材交给了苏联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但是由于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在苏联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长途迁徙转移途中将“影片大部分素材丢失”。袁牧之等人得知后,真是扼腕痛惜。后来我们只是1950年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中,才见到了《延安与八路军》中的个别弥足珍贵的镜头。
在苏联,袁牧之曾经作为苏联导演大师C·爱森斯坦的助手,参加了著名影片《伊万雷帝》的拍摄。曾经观看过《生死同心》的爱森斯坦对于袁牧之的表演才能非常赏识,他经常用袁牧之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之一的名字称呼他“天才的李涛”。在阿拉木图,袁牧之还编导了关于哈萨克伟大诗人江布尔的纪念影片,他以诗人的作品贯穿全片,结构影片情节,使这部传记影片像一部诗剧,很有新意,因此受到苏联同行的好评。在苏联长达五年的生活中,袁牧之与广大苏联人民一起经历了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艰难困苦,挨冻受饿是家常便饭,在生死关头他甚至感到过绝望,但是他终于坚持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并且在红场接受了斯大林的检阅。战后,袁牧之立即离开苏联回国,来到了正在筹建我党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的长春。
抗战胜利后,东北地下党组织团结在日本侵华期间在长春建立的电影文化侵略机构——“满州映画协会”(简称“满映”)中工作的中国爱国员工,于1945年10月1日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由延安派往东北解放区的田方、许珂、钱筱璋等同志根据命令,正式进厂进行接管,袁牧之担任了接管工作的顾问。不久由于战事的发展,我军决定撤离长春。为了保住东北电影公司这个党的电影宣传基地,袁牧之向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同志立下了与东北电影公司的全部财产共存亡的军令状。得到凯丰同志的批准后,袁牧之在战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找部队调到了车皮,还从东北新华书店调来了警卫部队,动员东北电影公司的大部分员工分批撤离,并尽可能地搬走了全部电影器材。
6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的全体职工携带全部器材到达位于佳木斯附近的兴山,他们立即开始了艰苦的建厂劳动,到10月1日,一个具有较完备设施的人民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建成,袁牧之在第一任厂长舒群调任他职后,担任厂长。
对于袁牧之来说,从他进延安的那一天开始,到后来在苏联学习生活的5年间,通过对苏联电影事业的考察,以及对于苏联共产党领导电影工作的经验的研究思考,他一直在考虑着人民的电影事业应当如何建立和开展。而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后,他开始有目的地探索并建立正规的电影企业,为全国解放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领导的国营电影产业打好基础。
首先,袁牧之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把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以及东北文工一团大批来自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调入东影,同时在东影创办了四期训练班,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这些干部与原来在伪“满映”工作的电影工作者一起,成为了“东影”这个人民电影基地的基本力量。随后,他正式提出并推动了“三化立功”运动。所谓“三化”,就是“正规化”、“科学化”和“统一化”。三化运动就是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讨论,探讨合理的分工和工作方法,并进而建立一套初步的管理制度,还用各部门制定的生产公约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和生产进行的保证。袁牧之又提出了“七片生产”的计划。所谓“七片”是指艺术片、新闻纪录片、教育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在当时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向前推进,解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新闻纪录片无疑是“东影”生产的重点,大批摄影队紧跟着部队前进的步伐,记录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与此同时,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新闻杂志片《民主东北》(共17辑)、第一部科学教育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等陆续生产出来,“东影”生产的幻灯片和新闻照片被源源不断地送往东北解放区各地和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当中。同时,一批长故事片,如《桥》、《回到自己队伍里来》、《中华女儿》等开始投入制作,这些影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影片。
在“东影”,袁牧之与同他自1934年起共同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影片的艺术上的合作伙伴,革命队伍中的战友,为人民电影事业战斗的同志陈波儿结为夫妻。
袁牧之投身人民电影事业,从一个党员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成为一位人民电影事业家。
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长
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始,解放战争的战略转折尚未来到的时刻,袁牧之已经开始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事业应当如何建设的问题。1948年9月,根据中央的指示,他给中共中央呈上了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中共中央收到报告后,在1948年底先后发出两份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指示肯定了袁牧之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设想,强调了用马列主义指导电影创作,把电影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还指出解放战争还有一年即可完全打败国民党,在加强新闻纪录片生产的同时,应当把对于国民党“国营”电影机构的接收和建立全国范围的电影领导机构的准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中央指示提出的加强新闻纪录片生产的要求,袁牧之在原有四个战地摄影队的基础上,又组建并派出了六个战地摄影队奔赴各地战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袁牧之于1948年12月28日又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二份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袁牧之对于国民党电影机构的接收提出了一套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接收方式的方针。除“东影”派出的以田方为组长的小组到北平接收国民党“中电”三厂,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外,袁牧之提出上海应“在地下党领导下由该地的电影工作同志负责接收”,并提出以该地进步电影工作者为主,组建一种有不同形式和任务的“第二种国营厂”;对于“经过清算而合法存在的”私营厂,他提出应争取其中之进步者,基本方针是“渐进与改良”。而这一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完成党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任务。
1949年3月,袁牧之奉中共中央命令离开“东影”来到北平,进行全国电影领导机构的筹建工作。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正式成立,袁牧之任局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局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下属的机构,成为国家电影事业的管理机构。在这时召开的文代会上,袁牧之向大会作了《关于解放区的电影工作》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并以副主席的身份兼管影协工作。
担任电影局长期间,袁牧之全面负责全国电影的初创工作。他工作的重点,首先是抓影片的创作生产,这当然主要是为了配合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在宣传方面的需要,以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也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影片从市场上赶走占主要地位的美国影片。无论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厂,都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形成了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影片的高潮。这几年生产的影片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工农兵群众在成为国家主人的同时,也成了电影的主人公。1950年生产的29部影片的产量和艺术质量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扩大了电影的影响。袁牧之策划了在全国20个大城市展出的“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这次展出的影片在群众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总理为“新片展览月”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人民电影事业的光辉成就》。新中国初期生产的一批影片,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上连连获奖,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还受到各国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让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了新生的新中国的形象。
针对当时许多人认为电影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当然应当由国家拨款的认识,袁牧之作为一个从事电影创作多年的艺术家,从事人民电影事业领导工作多年的事业家,为了保证新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力图使电影企业能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逐步达到国家少拨款乃至不拨款的目标,他在认真总结中国电影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中国电影事业实际情况、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奠定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管理体制的基础。
电影创作和制作,是电影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发行放映则是把影片推向市场的手段。为此,全国各大行政区分别建立电影经理公司。在袁牧之的精心策划下,电影局在南京举办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放映人员训练班,学习时间为三个月。训练班结束时,电影局购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出品的16毫米放映机,一次装备了600个流动放映队,真正做到了把电影送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
袁牧之不仅是一个实践家,他还是一位善于随时随地总结经验的理论家。就在新中国电影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在电影局成立研究室,还准备筹办两种刊物,一个是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一个是群众性普及性的刊物。同时为了让创作人员能够通过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而不断进步,他还制定了创作人员完成每部影片后必须进行艺术总结的制度。这些制度一直被实行至今,对于提高中国电影的质量不断起着切实有效的作用。
为了完成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工作,袁牧之在电影局组织的领导班子中,团结了各方面从事电影工作的领导同志,其中有吴印咸、田方、汪洋等与他长期在解放区共事的同志,也有蔡楚生、史东山这些从左翼电影运动时期就追随党的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有罗静予、官质斌这些长期跟党走的技术专家,还有袁庶华、彭后嵘这样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党的组织工作的同志,陈波儿担任了党总支书记和艺委会副主任。正是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团结共事,发挥集体智慧,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初创时期的辉煌。
袁牧之在电影局局长的位置上工作了整整三年,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病休生活
袁牧之几十年来为了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而忙碌奔波,久患肺结核与肺气肿,由于工作压力大,又疏于照料自己,他的身体状况严重不良,后来又患上了神精衰弱的毛病,一看电影就头晕头疼。于是,组织上提出让他离职休养一段时间,并且安排了接替他工作的人。在离职休养期间,袁牧之应中央宣传部分管电影工作的负责同志的要求,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生产的中心已经迁移到北京,可否考虑在北京的西北郊选择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电影村的设想。但是,由于他在离职休养期间,接任他工作的同志依照自己的推算,把袁牧之关于“电影村”的设想不适当地夸大为要建设成为一个需要4万多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大约12万人之多的“电影城”。这不仅不符合袁牧之的初衷,更不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并且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做了通报。正处在离职休养中的袁牧之虽然并不应当对于这个所谓“电影城”的设想承担责任,但是他因为自己仍然担任着电影局长,所以主动承担了责任。当袁牧之在病情稍有好转后回到北京时,已经不具备继续工作的条件,加之医生向他建议,如果要彻底治好身体,必须离电影越远越好。就这样,袁牧之向领导递交了辞呈,辞去电影局长领导职务。
离职休养的袁牧之一面养病,一面仍然挂念着电影创作,他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了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并准备创作的童话儿歌《小小环球》,并设想在此基础上拍摄一部按照唯物史观表现人类发展历史的影片。
早在1942年,袁牧之在苏联亲自经历了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的苏联军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目睹了人类经历的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次年他用俄文第一次写下了创作提纲。后来他回到祖国,一直忙于为人民电影事业而奔忙,但是这个创作意图在他的心中一直酝酿着。离职休养后,他立即投入了这个作品的创作。在这部作品中他以丰富的想像力,用通俗浅显的语言,用仅仅六个人物生动地概括了人类从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历史,显示出他用艺术形象表达思想的深厚功力。这部作品的创作成为袁牧之离休后这20多年生活的中心,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投入了全部精力,最后终于在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50周年前夕完成。
与此同时,他还在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了解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的风俗和文化,同时也就自己的创作征求当地同志的意见。这些经历也大大丰富了《小小环球》的创作内容。
在他休养的过程中,他经常观摩各个剧团的演出。一次在杭州,他的老友丁玲带他去看国风昆苏剧团的演出,他以一双艺术家的慧眼看出了这个团所演出的昆曲非常值得珍视。于是他找到戏剧界的领导人田汉,恳切地说:“昆曲快绝种了!”田汉乐观地对他说:“绝不了!”袁牧之建议田汉邀请剧团到北京去演出,田汉随即发出了邀请,丁玲在北京还写文章介绍国风昆苏剧团演出的昆剧。同时,袁牧之找浙江省的沙文汉省长,说服他同意国风昆苏剧团到北京演出,而且建议省里为剧团解决生活费和固定的住处,并添置了行头。为了进京演出,剧团选中了《十五贯》整理排练,该剧到北京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这部戏后来还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周恩来总理称赞这出戏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袁牧之的妻子陈波儿因心脏病于1951年去世,他结识了曾任国风昆苏剧团团长的女演员朱世藕,她当年在华东戏曲汇演期间是昆曲界最年轻的获奖者,袁牧之对她的表演非常赏识,经过一番交往,他俩结成了伉俪,他为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朱心。不久,年近半百的袁牧之作了父亲,他们的大女儿牧女继承父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到中国电视剧制片中心工作,她导演的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二女儿小牧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在新闻出版署从事版权代理工作,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研究生进修班学习;儿子牧男文学专科毕业,爱好文学创作,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自由职业者。
人民没有忘记他
人民没有忘记袁牧之,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对袁牧之的电影创作的成就,以及对于开拓人民电影事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期出版的《五四以来优秀电影剧本选》中,收入了他创作的《桃李劫》和《马路天使》的剧本。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作品经常被选送参加中国在国外举行的各种类型的电影展览,并且受到国外电影观众的欢迎和专家的高度评价。
1984年,袁牧之75岁诞辰之际,《袁牧之文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文集收入了袁牧之创作的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以及他早年的著作《演剧漫谈》和《戏剧化装术》,并且按照袁牧之的遗愿,发表了他20年心血的结晶棗童话儿歌《小小环球》。而就在此时,在一次新中国电影史志的编写会议上,袁牧之的许多老同事、老部下一起怀念起与他共事的时刻,并提出一定要把他的贡献写进新中国的电影史志里。
1989年,袁牧之80诞辰的时候,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为他举行了全方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广电部领导和与袁牧之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部下和袁牧之的亲属出席了纪念会。与会的老同志发言,深情缅怀袁牧之;青年学者发表论文,对袁牧之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这表明袁牧之的成就和经验作为中国电影文化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已经被新一代接受和继承。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举办纪念左翼电影60年的大型纪念活动,为这个纪念活动编选的文集中,袁牧之和他的作品,再次得到广大电影工作者的高度评价,他的作品也再次在电影院和电视台放映和播放,受到新一代观众的欢迎。
199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电影局领导同志和大批电影艺术家、学者和专家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共聚一堂,举行“新中国电影50年学术研讨会”,许多老艺术家和专家学者发言缅怀袁牧之,高度评价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的业绩,以及作为电影事业家的成就。中国著名的电影学术刊物《当代电影》在1999年国庆节出版的第五期将袁牧之作为封面人物,并发表了一组袁牧之的文章和论文,表达了对袁牧之的敬意和缅怀之情。
袁牧之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艺术家,他数十年的舞台与电影表演和编导艺术实践,他塑造的那些闪烁着动人光彩的艺术形象和活动影像,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财富。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不会忘记他,中国的电影观众不会忘记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
注释: ①②③ 引自《演剧漫谈》,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11月印行。 ④ 引自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原载《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⑤ 引自袁牧之《漫谈音乐喜剧》,原载《电通半月刊》1936年第10期。 ⑥ 引自袁牧之《创造者的苦心和观众》,原载《明星半月刊》1936年第7卷第4期。 ⑦ 引自《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